双男主角是傅芝钟刘蝉的纯爱人气小说《蝉》是由新锐作者妤芋独家创作的好书,这部乱世年上小说的文风很受读者的欢迎,CP人设是冷漠淡然老爷×娇蛮伶俐六姨太,《蝉》全文精彩内容概述:南国傅府有一位六姨太,是男的。此事虽惊世骇俗,却无人敢说六姨太刘蝉一句不是,只因他受尽宠爱。与傅芝钟在一起多年,刘蝉学会收起天真与任性,帮助傅芝钟打理傅府,虽然风光无限,但刘蝉终究是妾,他渴望着傅芝钟更多的爱,也想光明正大的站在他的身边。傅芝钟虽然爱惜刘蝉,却因为喜怒不形于色而看似无情,刘蝉每次期待都在傅芝钟平淡的反应中落空...更多精彩优质的小说尽在智能火~
免费阅读
傅府除夕是没有守岁的习惯的。
守岁也不过就是为了派个压岁包,放个鞭炮罢了。但是傅府院子里一个小孩也没有,那还守什么岁?
过了中午那顿走亲访友闹哄哄的宴席,晚上那场闭门谢客安静无声的家宴,一大家子人便也就散去自己的院子里。
四夫人计划着在自己的院里放些烟花,她约了七夫人李娟雅一块。
“这烟花,一个人看终究还是寂寞了许多。”她笑着拉起李娟雅的手,“妹妹和我同去赏赏烟花,吃吃茶可好?”
李娟雅当然点头答应。
于是,四夫人和李娟雅一块走去庭院中。
边走,四夫人还笑吟吟地与李娟雅说,“还好妹妹你来府里了,否则今年的烟花,我都不晓得找谁来陪我解闷了。”
李娟雅没把这句话放心上。
她随口客气道,“哪有的话,这还是承蒙四太太照拂我了。府里不是还有其她太太们?太太相约,她们定也是会欣然来赴的。”
四夫人露出一抹意义不明的笑来。
用了晚膳之后,天色早就晕染成了墨蓝,四夫人与李娟雅穿过漫长的小道,四处都不算明亮,只有路两边的灯笼还亮通。
也许是这昏暗灯光的影响,四夫人嘴角那丝笑意,落在李娟雅眼里,平白多出了几分神秘和几分熟悉……
好像刘蝉也经常在她面前露出这种笑,不过刘蝉笑得要更刻薄些——大多数时候,都是在笑她又说什么白痴蠢话了。
而四夫人的那笑也不过是转瞬即逝。
片刻后她又柔柔地开口,“那可不是这样的。”
她说,“这府上,大概只有我,总是寂寞得没有盼头。”
李娟雅一时怔然。
而不同于相携去院落里看烟火的四夫人与李娟雅。
在主楼待着的傅芝钟与刘蝉,就算是不去四夫人的院子里,站在二楼的小阳台上,也尽可把傅府里的光景一览而尽。
不过他们两人皆对那些,在夜空里稀里哗啦爆炸的烟花没有兴趣。他们早早便梳洗后,在床上亲密一番。
“傅爷,今年你予我包了多大的红包?”刘蝉趴在傅芝钟的胸前问他。
刘蝉的小脸上还带着些**过后的红,看起来明艳得过分。
傅芝钟瞥了他一眼,逗刘蝉,“你多大了?还找讨要压岁包?”
二十有二的刘蝉哼了一声,他才不管这些。
“我不管,不管!傅爷,我就是要红包!”他毫不讲道理,半是嗔半是娇地要求道,“要大的红包,比所有人都大,最大的!”
刘蝉说着又扒拉到傅芝钟身上,仰起头,睁圆了自己的柳叶眼望着傅芝钟,“傅爷难道不愿意给我吗?”
刘蝉说这话的时候,听着像是指责控诉。但在亲密之后,他的嗓音软和又有些沙哑,尾音稍稍往上翘,有一种说不出的楚楚可怜。
傅芝钟看着自己怀里不依不饶,泫然欲泣的刘蝉。
仿佛他告诉他,‘没错,自己真的未曾准备压岁钱。’刘蝉立马就能委屈得掉两滴眼泪。
于是傅芝钟只有伸出手指,点了一下刘蝉的额头,“你且去摸一摸你的枕头下,看看是什么?”
刘蝉闻言,他眨眨眼睛,空出一只手去探——
枕下正好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锦袋!
刘蝉摸了摸,这锦袋差不多有他手心那么大,布料光滑,上面绣着些什么花纹,丝线细腻。刘蝉的指腹从上面滑过时,能清晰地摸到每一根丝线的脉络。
摸到红包以后,刘蝉却没拿出来。
傅府里的规矩一贯是压岁包放在枕下过后,便不可取出的,否则便是‘活不过这一岁’的不吉祥之意。
人要压着,睡一晚上过后才能拿出。
讨到了压岁包,刘蝉脸上高兴了几分。,
“那傅爷,我是不是最多的?”他又缠上傅芝钟,噘嘴问,“傅爷,傅爷,你是不是给我包了最多的?我是不是比所有人都多?”
傅芝钟无奈地看了刘蝉一眼。
“你何时看见我给别人包了压岁?”他低下头看着刘蝉反问道。
刘蝉歪着脑袋回想了一会儿。
似乎今日正午,对那些带着自己幼子前来拜访的宾客,傅芝钟好像确实没有赠压岁包,而是送了些值钱的小玩意给那些孩子。
大多是什么和田玉雕刻的小动物像,看着稀奇古怪却也不算太昂贵,孩子们都挺喜欢。
意识到自己绝定是胜了那群收了傅芝钟压岁礼的小豆丁后,刘蝉整个人都身心愉悦了。
“我就知道傅爷对我是最好的!”刘蝉说着,支起自己的上半身,腻腻歪歪地叭叭亲了傅芝钟两大口。
傅芝钟瞥了瞥刘蝉,刘蝉亲完之后,就嘻嘻笑笑缩进自己怀里,一点也不害臊。
傅芝钟摇摇头,任由刘蝉的口水印留在自己的脸上。
刘蝉到底是比他小了十五岁,如今也不过是二十有二,正是活泼的年龄。那些年轻人在情绪高涨时,会做出的种种大胆举动,刘蝉也会做。
问完了压岁钱,刘蝉就又和傅芝钟聊了些别的。
主要还是聊明日祭祖的事情。
“傅爷,今年祭祖可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?”刘蝉问。
这个问题他已经问了百八十遍了。
虽说刘蝉负责后院的事项已然好几年,但他始终是忧心自己做不好让傅芝钟蒙羞。
祭祖这样的大事——明日与傅府有血缘渊源的人都要来——刘蝉是无论如何都要确保万无一失的。
傅芝钟看出了刘蝉眉梢间暗藏的焦虑。
傅芝钟知晓,这些天院子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刘蝉在处理,而刘蝉又谨慎,每每一件事情已经核对一遍了,他却生怕有差错,硬是要再核查两三遍。
也是辛苦他了。
傅芝钟抚了抚刘蝉瘦削的背,“你无须担忧,祭祖一事无甚特别之处,不用多家担心。”
刘蝉感觉到自己背后傅芝钟手心炙热的温度。
他像是被顺毛的猫,慢慢从心里不自觉的烦躁中放松下来。
“……傅爷说得是……但是,我这也是怕出现什么以外的嘛……”刘蝉嘟囔着,“明日有那么多人要来,还都与傅爷或多或少有血缘关系,这叫人怎么不在意?”
“要是出了什么岔子,比方说沈璐突然发疯又跑到山上去当她的尼姑,刘菊方那只臭猫,在祭祖的时候上蹿下跳,蹦到祭品桌上该怎么办?——外人不得又东说说,西说说,那些个市井里的闲人你一言,我一语,就有事个似是而非的故事了。”
刘蝉说着,右手大拇指的指甲,忍不住地不停划过食指的指尖,指甲划得一下比一下深,把食指的都划得泛白。
他身边的傅芝钟却没有急着说话,他在一旁安安静静地听完了刘蝉的种种絮叨。
等刘蝉叹出口气,总算是说完了,傅芝钟先捏住刘蝉的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,以防他用指甲划破自己的指尖。
而后,傅芝钟顺了顺刘蝉的头发,“我不在意之人,你亦不应在意。不敢直视我之辈,亦不敢取笑于你。”
“你何须担忧这些?”他说,“就算是不符合礼节,沈璐缺席,猫登祭台,我说我不喜沈璐,我说猫登祭台即是瑞祥,又有谁敢反驳?”
傅芝钟的语气平淡无奇,但其中的霸道却暴露无遗。
刘蝉从他的怀里仰着小脸,听得一愣一愣的。
“小蝉,如今已不是前面几年,这南国的光景早就换了。”傅芝钟垂眼凝视着刘蝉。
他的眼里是刘蝉熟悉的冷漠与淡然。
傅芝钟的眸色很深,每次他与刘蝉对视时,刘蝉就感觉自己在看一条长长的、漆黑的、看不见尽头的长廊。
那长廊不见一点光亮,也没有什么声音,寂静而暗沉。人踩上去除了脚下木头的咯吱声,就只能听见自己忐忑的呼吸。
刘蝉睁着自己的眼睛,眨也不眨地盯着傅芝钟。
这一刻在床头灯下低语的傅芝钟显得沉静极了,他的眉宇间充斥着一种上位者的平静和笃定。让人完全移不开眼。
傅芝钟轻拍着刘蝉的背,像一个长辈在哄睡小孩。
“你惧什么,忧什么?”他说,“前些年,我等守礼,不过是因为我等不是礼。而如今,我等守礼,也不过是尊祖制。”
“小蝉,你要再放肆一些才好。”傅芝钟淡淡地说。
刘蝉笑着轻轻嗯了一声,他的眉眼笑开了,全是温顺的软和。
其实刘蝉不懂得傅芝钟说的这些。
南国的那些什么局势、什么世道、什么尔虞我诈、你进我退,刘蝉其实都不太懂,这些年,他在傅府一直深居简行,对这些都不甚关心。
但是傅芝钟让他肆意一些,那他就会肆意妄为,会飞扬跋扈。
傅芝钟看着怀里乖乖巧巧的刘蝉,傅芝钟清楚,刘蝉一贯是听他的话的。傅芝钟环抱着刘蝉,怀里的刘蝉正用手指拨弄着他衣襟上的花纹,小声地又和他在抱怨着什么。
傅芝钟一边听着,一边静静地敛了目。
在他幽深的眼中,谁也不知道他在思索些什么。
每年傅府祭祖,都会莫名其妙地下小雨。清明是,春节也是。
傅芝钟执着伞,同刘蝉一起去祖坟那一大块地的后面——那个后面有两个小包,矮矮的,位置很偏僻。
刘蝉扒拉着他的手臂,他们深一脚、浅一脚地走过一道泥泞的小路。一路上的枯枝烂叶,被刘蝉和傅芝钟踩得噼里啪啦地响。
前面提灯的守墓人,和不远处负责警戒安保的侍从都安安静静的。除了雨的淅淅沥沥、泥巴粘上鞋底又脱落的声音,没有其它的声响。
刘蝉看着前面穿着蓑衣的守墓人,他提着的灯被雨水朦胧,提灯被模糊成了一团光亮,在前面悠悠,这团光有毛毛的、却不清晰轮廓。
刘蝉抬起头,去观身边傅芝钟的神情。
每年在傅族的大祭后,单独弯弯绕绕来到这处扫墓时,傅芝钟面上的表情便会尤为寡淡。好像这人世间所有的喜怒哀乐,都离他远去了一样。
曾经他在刘蝉面前,偶尔又难得流露出来的情绪,都似乎是刘蝉的错觉。
也许因为伞是黑色,刘蝉看不太清傅芝钟的神情,只能窥见他面上沉着的一片阴翳。
不过刘蝉猜,今年傅芝钟的神情依旧是寡淡的,冷冷清清。和伞外静谧细密的雨一样。
这样想着,刘蝉扒拉紧些了傅芝钟的手。
其实,按照辈分,这两个小包不该在这么偏远的地方的。只是那个先走的孩子是夭了,不太吉祥,当年怕坏了风水,位置就偏了些。后面那个孩子,傅芝钟担心他一个人在地底下太寂寞了。便埋在了他的孪生姊妹身边。
在傅族内大祭时,祭祀的桌子上也有这两个孩子的牌位,他们也是受了祭祀,受了人间的祭拜的。这两个孩子的名字,都还是傅芝钟一前一后刻上去的。
但傅芝钟不放心,他说,那些烧的纸钱没有飘到这边来。瓜果点心也放在祭台上,离得也太远了些。
说这话的时候,他的神色平淡,看不出什么心痛不心痛。
不过是一种很沉静又克制的担心罢了。
“小蝉,你拿着伞。”
到了那两作小包,傅芝钟把手里的重重的伞递给了刘蝉。
这伞是好伞,真材实料,多大的风都掀不起一点伞面,就是太沉了,刘蝉拿着有点吃力。
“莫要淋着雨了,容易着凉。”傅芝钟嘱咐说。
刘蝉嗯了一声,接过伞,他乖巧地退到一边,看傅芝钟接过守墓人的篮筐。
那篮子里装着两碟点心,和几大捆敲了铜钱印的黄票。
守墓人识趣地行礼后就退到远远的,不来打扰。
傅芝钟先把两碟点心放好,而后便点燃了一捆黄票。
黄票易燃,就算是在阵阵的雨下,只需一丝火苗,它也能燃起来。
傅芝钟半蹲下来,他耐心地把手里的黄票一张又一张覆进火苗里。
站在一旁的刘蝉默不作声地看着黄票燃后的灰烬飘起来。灰烬纷纷扬扬的,乘着风带着雨水的重量,飘了又落下。
刘蝉凝望着半蹲在那两个小包前的傅芝钟。
傅芝钟低着头,还在烧纸钱,看不清他的神情。
但刘蝉想,傅芝钟应当是在神伤的。
毕竟那两个小包里都躺着他的稚子,两个都是死于无妄之灾。
傅芝钟以前与刘蝉说,他说,他幼时有个算命先生说过,他命中无子,是孤独的相。那时他年轻,没放在心上,现在看来,或许一切都有着命数。
‘可是,’傅芝钟说,他转头看向窗外,目光深远难测,‘我是这样的命数,又为什么要为难两个孩子?’
‘若是一开始,他们就没来这个世上便好了。平白走了一遭,却尽是受罪。’他说。
彼时,刘蝉坐在傅芝钟的怀里,把自己的手搭在傅芝钟的手上,轻声说,‘傅爷,这不是你的错。’
傅芝钟看了刘蝉一眼,他没说什么,只对刘蝉摇了摇头。
那摇头,不知道是在否定刘蝉的话,还是在肯定刘蝉的话。
刘蝉举着伞,这伞大而沉,刘蝉手都累了,只得把它搭在肩上。
傅芝钟烧完了自己手里最后的一张黄票,他站起来,走到刘蝉面前。
他淋了许久的小雨,丝发间都带了些晶莹。
“可累了?”傅芝钟接过伞,缓缓问道。
刘蝉摇摇头,“傅爷,不累的。”
他说着,不管有些发酸的小臂,又攀上傅芝钟的手。
傅芝钟领着刘蝉往那两个小包面前走。
“小蝉,这是傅早枣,要早出生一些,”傅芝钟指了指他们右边的小包,“是我的长女。”
“这是傅晚玉,”他又指向左边的小包,“是我的长子。”
每一年,傅芝钟都要向刘蝉介绍自己的两个孩子。
这两个小包有些差别,傅早枣的小包是土筑的,那意味着尸身在下。而傅晚玉的小包是木头搭的,那说明这是衣冠冢。
刘蝉眨眨眼睛,他和每一年一样,对两个小包俯了俯身,依次喊了声,“小姐”和“公子”,然后介绍自己说是傅爷的六夫人,叫刘蝉。
傅芝钟看着刘蝉,他的视线很轻地落在刘蝉的身上。
从傅芝钟的视角看下去,能看见刘蝉乌黑的发顶,以及他密密扑闪的眼睫。
傅芝钟记得,自己第一次见到刘蝉时,刘蝉套了一身的女装,抹着胭脂。他瘦弱,营养不良,脸色泛白,满身的懵懂又俗气,说不上有多好看。
只是那会儿,是刘蝉那头披着的长长黑发慑住了他。
刘蝉的头发很好看,不仅长而多,更是乌黑亮眼,根根头发顺下,握在手里就好像分流的黑色的小河。
刘蝉的头发天生就好,如果说发好就是命里富贵是真的,那刘蝉怕是富贵命中的富贵命。他的发在灯光下染着光晕,晃得人移不开眼。
傅芝钟当时注视着刘蝉想,如果傅早枣没有夭,傅晚玉没有死,那他们也许也是有这么一头漂亮的长发的。
不过他们肯定会比面前这个男孩健康,脸上也没有浮萍一样的张皇。他们约莫是张扬的、开朗的、又懂得规矩、知书达理的。
刘蝉感觉到傅芝钟的默默的注视。
他扬起小脸,有些困惑地望着傅芝钟,不知道傅爷怎么一直盯着他看,是有什么事情吗?
傅芝钟感受到刘蝉的询问,转回视线,敛目摇了摇头。
是无事的意思。
于是刘蝉便也不多问。
他陪着傅芝钟站在这两个小包前,又站了许久。
沈璐总是抗拒祭祖时到场,若不是今年刘蝉直接威胁她,她又会像去年那样,托辞避去寿山的尼姑庵的。
沈璐避开的原因倒也很简单。
就是因为这两个小包,就是因为傅早枣与傅晚玉,这两个她生育的、还没学会说话就去了的孩子。
刘蝉盯着傅早枣那个小小土包。关于傅早枣,除了极个别,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这孩子是从母胎里出来身体不好,不幸夭折了。
但是,事实并非如此。
刘蝉这些年,一直在好奇,当年沈璐究竟是怎样的心态,去活生生掐死自己的女儿的呢?
他不懂得这些。
在子女与父母,在妻子与丈夫这些关系上,沈璐究竟是值得恨呢,还是值得怜悯呢?
刘蝉也不懂得这些。
“小蝉,走吧。”傅芝钟拍了拍刘蝉的手,打断刘蝉的思绪。
刘蝉回神,轻轻地嗯了一声。
他挽着傅芝钟慢慢向外面走去。
雨还在阴郁地下,路上的泥也更稀了些。
快走到守墓人那边时,刘蝉悄悄回头看了一眼那两个无声的小包。
两个小包的中间烧了一堆高高的黄纸。包两边各自摆一碟,上面都整齐又平均地垒着糕点。是小孩子会喜欢吃的那些糯米食。
刘蝉摸摸自己的心口,他垂下眼想,他确实是羡慕傅早枣和傅晚玉的。
傅早枣和傅晚玉,来这世上这么短短的一遭,却还是有人记住,还是傅爷记住他们。
但是他呢?刘蝉心想,他要是死了,可能什么都不剩了。
姨太太是进不了傅族的墓地的。他死了过后就成了灰,傅芝钟在这个墓地的大院子里,他也不能靠近他,他在外面就成为一捧尘埃。没谁会记住的那种。
不过这样的羡慕实在是太越界了。
刘蝉放下摸着自己心口的手,毕竟傅早枣和傅晚玉是傅爷的孩子。
而他只是个姨太太。
不应该去想要这么多的。
刘蝉在心中说。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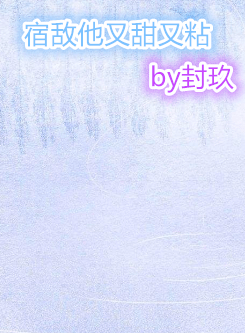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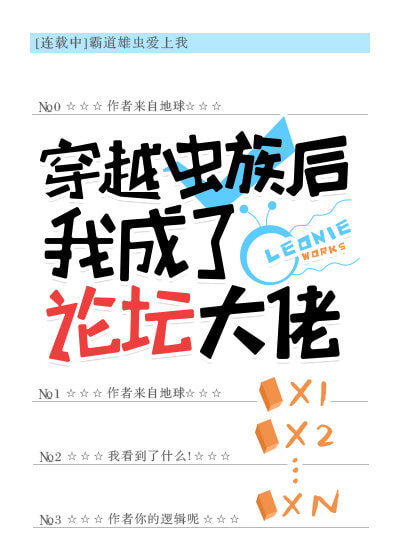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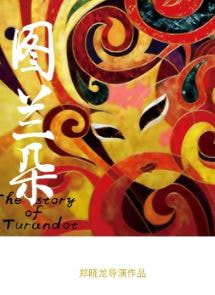



智能火网友
感觉还行。
智能火网友
大大加油啊。看得出来功底还是很深厚的。
智能火网友
为什么呢>_<
智能火网友
(*^▽^*)
智能火网友
因为上学,实在没办法看你的文,而且我已经初三了,要迎接中考了,实在放不下你的文,好纠结啊
智能火网友
你等一下,我问问作者
智能火网友
阿玖♡新开作品啦!不要太累♡真的是会心疼♡ 爱你的阿城♡
智能火网友
大家好 我是第二个作者
智能火网友
文笔超好. 脑洞超大. 就是有点懒.
智能火网友
蛮期待(๑˙ー˙๑)